来源:今日头条

学人小传
黄药眠(1903—1987),广东梅州人。诗人、文艺理论家、美学家、教育家。1925年毕业于广东大学,后加盟“创造社”,1929年在苏联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任翻译,1933年回国,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国际新闻社总编辑、“文协”桂林分会秘书长、“文协”香港分会主席、《光明报》主编等。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著有诗集《黄花岗上》《桂林底撤退》,小说《淡紫色之夜》,散文集《美丽的黑海》,文艺论集《论诗》《论约瑟夫的外套》《初学集》《迎新集》等,口述自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图片由作者和黄药眠家人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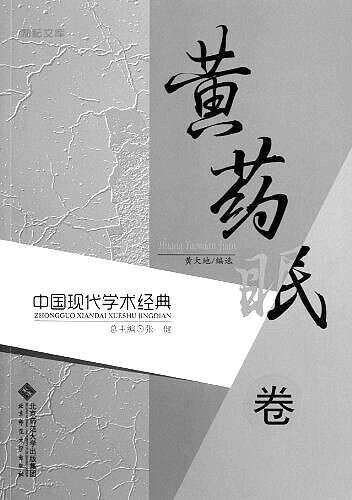
图片由作者和黄药眠家人提供

图片由作者和黄药眠家人提供

20世纪40年代,黄药眠(二排右二)与达德学院学生在一起。图片由作者和黄药眠家人提供

黄药眠(中)、钟敬文(左)等在一起。图片由作者和黄药眠家人提供
【大家】
他是诗人,从小沐浴在岭南诗风中,青年时期因诗歌才华崭露头角,得到成仿吾赏识,成为创造社的一员;他是文化战士,他创作的诗歌、小说深度介入“文艺大众化”“文艺民族形式”“文艺主观论”等论战,发出革命者的呐喊;他还是文艺学学科的开拓者,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文艺理论教研室,编写了第一个高校文学概论教学大纲,主持了新中国第一个文艺学研究生班。他就是早在抗战时期便被人们尊称为“黄大师”的北京师范大学文科一级教授——黄药眠。
忆及老友,史学家唐振常说:“朋友们都称黄药眠先生为黄大师。我不明白这个称号的由来,大约是赞扬他的博学多才。他也因此而取大师二字的谐音,以达史为笔名之一。的确,黄大师是一位多面手。在文学领域里,早年即以琅琅可诵的漂亮的散文闻名于世,兼写文艺论文,鞭辟入里,富卓识高见。又擅长写作国际国内时事政治论文,常言人之所未言,发人之所未发之覆。还从事新闻工作,为桂林国新社的一员战将,兼办杂志,做编辑。全国解放之后,长期执教大学,培育英才,功在教坛。”
在编撰黄药眠年谱的过程中,爬梳细读各种文献史料,这位“大师”身影如唐先生的素描一样慢慢浮现在我眼前。
创造社里的岭南才子
1903年,黄药眠出生在粤东北嘉应州(今广东梅州)一个偏僻小城。据黄药眠自述,“我的母亲是被人放在草堆里的弃婴”,“我的父亲是谁,我也不清楚。因为我的母亲等来的‘郎’,是个白痴,后来他就到南洋去了,而且一去就永无消息”。尽管家境贫寒,不识字的母亲却晓得读书的好处,因而时常带他去旁听童生和秀才们说唱“西厢”“聊斋”。后来的一天,他竟自己念起《西厢记》里的词句来,秀才们很是惊讶,向他的母亲建议:“这个孩子可以读书。”于是,黄药眠开始了读书生涯。
自1911年秋至1921年夏,黄药眠先后在梅县县立高等小学和梅州中学求学。那时正值“五四”前后,风起云涌的新文化浪潮也吹到了梅州。他除了对楚辞、汉魏乐府、六朝小赋、唐诗等学校里讲授的古诗文兴趣浓厚外,还被泰戈尔、冰心的新诗深深吸引。梅州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更撞击着他的心灵,作为岭东学生联合会梅县分会的秘书长,黄药眠在当地爱国学生活动中扮演着骨干角色。
因家庭经济拮据,中学毕业后,黄药眠考入免收学费的广东高等师范学校英文系(毕业前更名为“广东大学”)继续求学。大学期间,他醉心于伯格森和尼采的生命哲学,还阅读了彭斯、华兹华斯、雪莱、拜伦等浪漫主义诗人的名著。在中西浪漫主义文学滋养中,黄药眠开始写诗。继《诗人之梦》后,他接连创作出《海之歌舞》《东山晚步》《赠东堤的歌者》《黄花岗上的秋风暮雨》《小酒家夜饮》《夜半归人》等自然清新又充满诗韵的佳作。这使得黄药眠成为校园里有名的“才子”,还得到其时在广东大学任教的创造社成员成仿吾、王独清等人的赏识。
1927年夏,王独清从广州重回上海接替郁达夫负责创造社事务不久,便选择发表黄药眠大学期间创作的诗歌《晚风》,并特意加发了“按语”:“我们这次到了广东,毕竟不算空去:因为认识了许多无名的青年作家。只就我个人来说,虽然还是两手空空地折返到上海,但一想到这层,倒真像是发现了宝藏而归,心中感着无限的安慰。黄药眠君也正是能使我们得到安慰的一个人,他底诗,要算据我所知道的广州青年底作品中最有希望的。我这次到上海来,带了许多广州青年朋友底作品,但在这许多的礼物之中,只有黄君的最为丰富。我将陆续地给他选择发表。现在先借这里郑重地介绍这位诗人,并望黄君继续努力。”(《洪水》半月刊三卷32期)
1927年9月,在大革命失败的浪潮中,黄药眠应成仿吾之邀来到上海,正式加盟创造社。在创造社出版部期间,黄药眠在工作之余重新整理了1923年至1926年间创作的36首诗歌,由此形成其处女诗集——《黄花岗上》。这部诗集于1928年5月出版,影响很大,奠定了黄药眠在诗坛的地位。茅盾称赞这部诗集“既有自由浪漫的现代情怀,又兼具楚辞的古风雅韵”。作家秦牧认为:“梅县是有名的民歌之乡,近代史上,诗人不断涌现。在我看来,自清末以来,最杰出的诗人,除了黄遵宪外,就得算黄药眠了。”
年轻同志的“黄大师”
黄药眠祖屋紧邻黄遵宪故居“人境庐”。黄遵宪这位喊出“诗界革命”的晚清思想家在时代巨变中探寻真理、救亡图存的爱国情怀,同样流淌在客家后人黄药眠的血脉中。
在创造社,黄药眠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书籍,还翻译了屠格涅夫的小说《烟》、格莱哥里夫人的独幕剧《月之初升》、辛克莱的长篇小说《工人杰麦》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说:“是马克思主义打开了我的眼睛,让我看到了整个世界。”
1938年11月,黄药眠辗转抵达桂林,任国际新闻社总编辑和“文协”桂林分会秘书长。桂林作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文化重镇,当时汇集了艾芜、艾青、田汉、夏衍等一大批文艺工作者,文艺创作盛况空前。然而,国统区文艺在黄药眠看来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抗战诗歌陷入“革命的空喊”,并在西洋流派影响下“空泛地追求形象,华彩和刺激”,导致诗歌走上歧途;二是文艺思想领域“主观战斗精神论”影响巨大。对此,黄药眠一边组织大量讨论,如“文艺的大众化问题,民族形式问题,民间文学问题等等;还组织了文艺讲习班,召集一些青年来培训,请一些老作家来做报告或讲授一些创作经验”,另一边则身体力行地通过著述来进行回应。
1944年出版的《论诗》共收入黄药眠1939年至1942年间撰写的14篇诗论,是他出于“诗人”经验又立于“革命者”的高度对诗歌理论问题的集中把脉。该书对抗战以来诗歌在美学艺术上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诊断,较早确立了诗歌的审美标准和诗歌民族形式的发展方向,还为诗歌之主题形式、分段分行、长句短句、音节格律、语言文法、审美习惯等创作技法提供了独具一格的经验法则,更为青年诗人提供了理论操演。
1948年出版的《论约瑟夫的外套》收入1943年至1947年间撰写的7篇论文,是黄药眠对“主观战斗精神论”的系统批评。黄药眠回忆说:“首先要搞明白,这个主观是什么阶级的主观,如果不研究清楚作家的阶级观点是什么,而拼命去提高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这是非阶级论。它不仅抹煞作家的阶级立场,模糊作家的阶级意识,而且助长文学上的个人主义,不利于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尤其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延安传播到国统区,黄药眠更“接受了这些观点,并宣传这些观点”。据此,黄药眠接连发表《读了〈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以后》《论约瑟夫的外套——读了〈希望〉第一期〈论主观〉以后》《论文艺创作上的主观与客观》等系列文章,对“文艺主观论”进行集中反驳。不仅体现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分析解决文艺问题的自觉,还得到茅盾的高度评价,“这是驳斥舒文的若干论文中间最好的一篇。好在什么地方?好在层层剖析……也就博得了若干共鸣,余音袅袅,至今未绝(特别是因为它穿上了‘约瑟夫的外套’)”。
1944年,桂林沦陷,黄药眠辗转昆明、曲靖、贵阳再由柳州乘船撤退到广州。在尝尽艰辛冷暖后,结合撤退过程中所见所闻,黄药眠在广州创作出被称为“抗战史诗”的《桂林底撤退》。该诗长29章、近1600行,以撤退、疏散、逃难为线索,多方位、全景象刻画出1944年桂林大撤退时的一幕幕场景,真实逼肖,写尽了战争中百姓生死别离的苦难,揭示出社会矛盾。该诗开篇吟道:“我愿意自己/变成一个巨大的竖琴/为千万人的悲苦/而抒情!”这一深情呐喊,不仅表达出黄药眠对祖国人民深沉的爱,还将其“为人类解放事业而歌”的革命理想淋漓尽致地传达出来。该诗1947年正式发表后,在文艺界引发轰动。
1946年3月,黄药眠离开广州抵达香港。在香港,他出任“文协”香港分会主席兼民盟中央机关刊物《光明报》主编,发表了大量国际国内时事评论文章。为培养革命人才,黄药眠又参与创办香港达德学院并任文哲系主任。据杨济安回忆:“文哲系在达德学院是个小系,但很活跃。系主任黄药眠先生治系有方。他请茅盾、曹禺、夏衍等著名作家来校作报告。有一次他把郭沫若请来,用一天工夫把从古到今的中国文学史讲了一遍,讲得精彩极了,博得阵阵掌声。他还把留港的文艺界知名人士如林默涵、臧克家等二三十人请到学校来,与全系师生举行座谈和文艺联欢。”“黄先生当时在香港文化界名气很大,特别在文艺理论方面是颇有权威的,人们尊称他为黄大师”,尽管黄先生非常忙碌,却仍然主讲“文学概论”课,“每周授课三四小时”,“每次讲完课都在学校住上一两天,利用课余时间进行辅导,解答问题,还和个别谈话,了解学生们的思想和生活情况”。
从桂林到香港,黄药眠的立德、立言、立行,有口皆碑,在青年中威望极高。正如他的老友林焕平所言:“药眠同志是后期创造社的诗人、活动分子,在文坛上,也是青年诗人的前辈。因此,这群广州的青年诗人都称他为‘黄大师’。以后在桂林、香港,年轻的同志都这样称呼他。”
对于在历史洪流中的抉择,黄药眠在自述中写道:“过去自己一天天苦闷彷徨,对于国家危亡和人民困苦,只是有些同情,只会自己叹息,而无可奈何。所以认识到这些以后,就决心跟共产党走。愤然把那些忧愁、哀叹、彷徨、苦闷都抛到垃圾堆里去,决意为中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献身。”
文艺理论的“拓荒者”
1949年5月,为革命漂泊半生的黄药眠受邀抵京,先后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和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当年10月,他在天安门城楼亲眼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在新中国,黄药眠主动选择投身教育事业,被聘为北京师范大学文科一级教授、中文系主任。据童庆炳先生回忆:“在他的亲自指导下,1953年北师大率先在全国成立了第一个文艺理论教研室,他亲任教研室主任,同年受当时教育部的委托牵头编写高校第一个文学概论教学大纲,1954年主编了当时在全国影响极大的《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1956年又第一次招收了新中国的第一个文艺学研究生班,1957年反右运动之前,又领头举办了新中国第一个美学问题系列讲座……”这些筚路蓝缕的工作,件件关乎学科大局,尤其是教材建设,在黄药眠看来“是文艺理论上的基本建设,很重要,很有意义”。黄药眠主编的《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不仅有效调整了苏联文论框架模式,还充分吸纳中外作家、理论家的经典言论,有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与古今中外文艺实际的结合,成为很长时期国内学习文艺理论的必备书籍。
文艺理论教学关乎人才培育,黄药眠因此格外重视这项工作。北京师范大学程正民将黄药眠的教学理念总结为“重马列、重传统、重实践、重能力”四个方面,这些特质清晰体现在他对学生们的言传身教上。孙子威在《学人楷模一代宗师》中回忆说,“先生教学注重务本,一贯坚持马列”且“注意抓治学的方法”,譬如“不要只读理论,还要多读作品,要读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风格流派的作品,还要学会创作,懂一点创作的甘苦”。龚兆吉在《缅怀先生两三事》中也提到:“在1957年以前,先生带研究生、进修教师时期,规定每月一次学术交流座谈会,汇报评说报刊上所发表的评论文章、新出版的重要作品和文学动态,文学理论教研室人员必须出席发言……讲课不能只讲我国古代的《诗经》《楚辞》、杜诗、《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方的巴尔扎克、左拉、狄更斯、托尔斯泰、高尔基;鲁迅、茅盾、郭沫若固然要讲,现在的作家作品绝不可忽略,尤其对当前有争议的作品必须讲,以防止将学生引向故纸堆中去而忘了现实。”
1956年7月,《文艺报》连载刊出黄药眠的《论食利者的美学——朱光潜美学思想批判》,他成为美学问题争论的“点火者”,拉开了“美学大讨论”的序幕。为响应“双百”方针,同时更好地进行美学问题的争鸣,黄药眠又在北师大中文系举办“美学论坛”,先后邀请“美是客观说”“美是主客观统一说”“美是客观社会统一说”的代表性学者做了7场报告,均由他亲自主持,现场座无虚席,引来《光明日报》《文艺报》等媒体报道。尤为重要的是,这些报告讲稿经整理公开发表后,产生巨大影响,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话语建设起到促进作用,还进一步助推了当时美学讨论的进行。
1957年5月27日和6月3日,作为中文系主任和“美学论坛”主持人,黄药眠也做了两场报告,演讲题目依次是“看佛篇”和“塑佛篇”。在“看佛篇”演讲中,他主要介绍苏联美学研究状况,并对美学论争中诸家观点进行评议。所谓“塑佛”,很明显,黄药眠试图先“破”后“立”,在对“各派”美学批评之后系统阐明自己的美学观点。据此,“塑佛篇”的演讲依次从美是什么、美与美感、形式美、自然的人化、审美能力、审美个性、艺术美七个方面集中阐发了“美是审美评价”的理论构想。遗憾的是,反右运动突发而至,黄药眠还没来得及整理发表讲稿就被错划为“右派”,直至1999年讲稿才由《文艺理论研究》和《文艺研究》陆续刊出。然而,历史的雾霭总会在时光的吹拂下散去。正如近一个甲子后童庆炳在《中国20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的第一学派》(《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的,“我们发现50年代的所谓‘四派’实际上都是认识论派,唯有黄药眠的观点——美是‘审美评价’转到价值论来讨论美学问题,不是认识论术语的生搬硬套,而是对认识论美学简单化有所批评”,因而“在中国美学发展史上,开启现代美学的价值论,是前辈学者黄药眠的贡献”。
1978年后,已步入古稀之年的黄药眠,在历尽磨难后身体已经很虚弱,却仍争分夺秒地重新投入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中。他不仅出版了长诗《悼念》(1980)、散文集《面向着生活的海洋》(1981)、小说集《淡紫色之夜》(1986),还陆续推出了《迎新集》(1983)、《黄药眠文艺论文选集》(1985)和《黄药眠美学论集》(1991)等学术著作。
尤其是在筹备“高等学校文艺理论研究会”(现为“中国文艺理论研究会”)和创办《文艺理论研究》过程中,德高望重的黄药眠发挥了重要作用。据华东师范大学徐中玉回忆:“药眠先生是文坛前辈,在创造社活动中已崭露锋芒,我在30年代初读大学时已从创造社的出版物中读到他的论文……40多年来,我一直非常敬仰他,也承他厚爱,多得指导。”中间有20年,二人没有往来,直至筹组“高等学校文艺理论研究会”,他们又开始一起工作了,徐先生说:“这已是1980年的事情。周扬同志担任研究会的名誉会长,荒煤同志被推为会长,药眠、陈白尘和我被推为副会长,我兼秘书长。《文艺理论研究》出版时,荒煤为主编,药眠、白尘和我为副主编,因为是在上海编辑发行,具体工作我多做些,经常同药眠先生商量,请他指教”“后来他因高龄,旅行不便,就没有再直接参加了,但对会务编务仍很关心。同行们也非常挂念他的健康,常问我:‘黄大师近来身体可好?’”一个社团和一份刊物,从无到有,其难度不言而喻。通过与同行合作,黄药眠的这些拓荒性工作历尽艰辛,利在千秋。
作为国家授予的我国第一批文科一级教授和首批文艺学博士生导师,黄药眠培育了大批文学理论人才。正如黄先生培养的博士生王一川教授所言:“黄药眠先生完全称得上是新中国文艺学学科体系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正是他的开拓和奠基工作,北京师范大学和全国的文艺学学科得以走上一条前所未有的新道路,直到他亲手建立起中国第一批文艺学博士学位授权点,而我等后辈则有幸成为这个学科园地里生长的桃李。”
在散文集《面向着生活的海洋》中,黄药眠写道:“教育工作者,用自己的身体搭成人梯,让后代的人一个个踩着自己的肩膀攀登,有些人可能一直攀登到智慧的峰巅。”黄药眠本人,既是创造者,也甘做人梯,他的一生,革命着、写作着、教育着——面向着文学的海洋。
(作者:李圣传,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