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凤凰网》 2021-05-21

使人们成为哲学家的动机多种多样。最值得尊重的则是了解世界的愿望。这种动机在古代占了优势,当时哲学与科学难分。另一种动机是感性的迷惘,这在古代是一个有力的激励。
诸如这样的问题:彩虹究竟在哪里?事物真的像它们在阳光或月光下显露的那样吗?这个问题较为现代的提法是:事物究竟像肉眼看到的那样或是在显微镜下看见的那样?类似的疑惑很快被更大的问题补充。
当希腊人开始怀疑奥林匹斯山的诸神的时候,便有一些人从哲学中寻求可以取代传统的那些信念。通过上述两种动机的综合,哲学中便出现了一种双重运动:一方面原先日常生活中不少被当作知识的并非真知;另一方面,大多数哲学家认为存在一种更深刻的哲学真理。
对于几乎所有的哲学,疑问一直是鞭策力量,确信则是终极目标。人们对感觉、科学和神学一直存有疑问,一些哲学家对这个疑问更关注,另一些则对那个疑问更留心。他们针对这些疑问提出的解答有着极大的分歧,甚至怀疑能否给予任何解答。
所有这些传统动机都曾引导我致力于哲学,但有两种对我影响尤深:一是产生最早也持续最久的动机,即渴望能发现某些知识是千真万确的;另一动机是渴望找到对于宗教冲动的某种满足。
我认为促使我对哲学感兴趣的第一件事发生在我11岁的时候(尽管那时我还不知道“哲学”这个词)。由于我的哥哥比我大7岁,我的童年总的说来是孤独的。毫无疑问,孤独的时候多了,于是我变得很严肃,也有许多时间去思考问题,只是没有多少知识可使我的思考派上用场。

当时我并没意识到论证给我带来乐趣,而且有数学头脑的人往往如此。长大后,我发现别人在这一点上也与我持有同感。我的朋友吉·哈代是位理论数学教授,对论证享有更浓厚的乐趣。
他曾告诉我:假如他能发现我会在5分钟内死去的论据,他当然会因失去我而难过,但是他从论证中得到的乐趣会远远地超过他的悲痛。我完全赞同他的看法,一点没有生气。
在我开始学习几何之前,有人告诉我几何可以求证事物,因此当我哥哥说要教我几何时,我感到非常兴奋,在那个年代,几何仍是“欧氏”几何学。我哥哥从定义开始,我学的也够快的。可当他接下去教定律时,他说:“这些是不能被证明的,但得以它们为假设,其他的定律才能被证明。”
听到这些话后,我的希望破灭了。我曾想要能发现可以证明的事物该有多好,可结果却要通过没经证明的假设才有可能办到。我有点愤慨地望着哥哥,说道:“如果这些假设不能被证明,我干嘛要承认它们?”
他回答说:“得啦,你要不承认它们,咱们就没法往下进行。”我当时想:先看看往后是怎么回事还是值得的,因此暂时就承认了这些定律吧。
可是,对于这个我曾希望是一清二楚的领域,我一直充满怀疑,迷惑不解。虽有怀疑,可我经常把它们抛在一边,总是设想这些疑问是可以解答的,只不过我尚不知道答案而已。
这样,我从数学中寻找到极大的乐趣——实际上比从其他任何学问得到的乐趣大得多。我喜欢设想将数学应用于物质世界,也曾希望有一天会出现与机械数学同样精确的人类行为数学。
我怀有这个期望是由于我喜欢论证,这心愿更多时候超过了我深切感到的对人的自由意志的渴求。尽管如此,我却从未彻底克服我对数学的确实性的基本怀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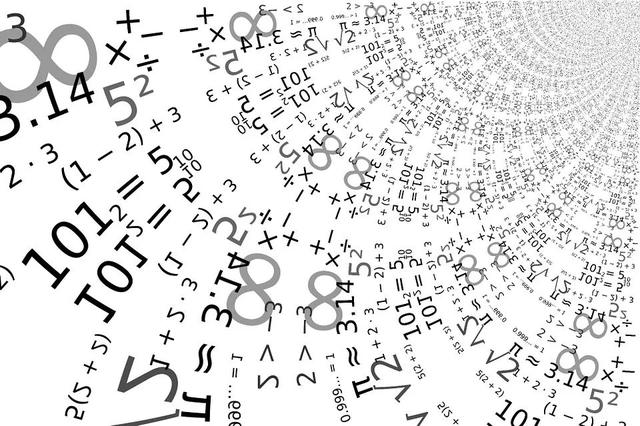
我开始学习高等数学后,新的困难便向我袭来。老师给我提供一些证明,可我却认为它们是靠不住的;后来我听说它们果然被证实为谬误。当时我不知道,离开剑桥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也不知道:德国数学家已发现更好的证明。
因此,对于康德哲学的大胆求证,我一直心领神会。它向我显示了一个崭新的辽阔视野,以前困扰我的种种困难都显得十分琐碎,无足轻重了。只有在我自己深深地陷入玄学的泥潭之后,我才认识到这一切统统都是不可靠的。
促使我转向哲学的则是我对数学的厌恶,因为它过分地专注于考试所需要的技巧。掌握考试技巧的努力使我把数学视为需要巧妙应付和机智对策的东西,总的说来太像纵横填字游戏。
在剑桥大学的第三学年末,当我考完最后一门数学的时候,我曾发誓永远不再理睬数学,而且把所有的数学书籍统统卖掉。在这种心境下,涉猎哲学给予我的喜悦犹如从山谷爬出而见到新的风景一般。我不光从数学寻求肯定的结论,正像笛卡尔(他的著作当时我尚不了解),我认为自身的存在对我自己来说是明确的。
像他一样,我感到可以假定外部世界只不过是一个梦。但即便如此,它却是一个真正做过的梦,而且我所经历的梦境仍然真切,历历在目。我第一次产生这种想法是在16岁的时候,后来听说笛卡尔把这当作他的哲学基础,我感到很高兴。
我在剑桥对哲学的兴趣得到另一动机的刺激。使我对数学都表示怀疑的怀疑主义也使我对宗教的基本教义产生疑问,但是我热切地渴望能找到某种至少可以把宗教信仰保留下来的东西。
15岁到18岁这段时间,我用了许多的时间来思考宗教信仰的问题。我逐个地对基本教义进行考察,真心地希望能找到接受它们的理由,我在一个笔记本里记下我的想法,现在仍然保存着这个本子。
诚然,那些想法粗浅幼稚,但它们所暗示的不可知论当时我却找不到答案。在剑桥,我接触到以往不知的所有思想体系,我也曾一度放弃我在孤独中产生的那些思想。在剑桥,我了解了黑格尔的哲学,在他的19卷深奥的著作里,黑格尔声称已经证明了一些东西,满可视为传统信念经过修正的精致的翻版。
黑格尔认为宇宙是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他所谓的宇宙像一块果冻,如果你碰到它的任何一个部位,整个果冻都会颤动;然而它又有不像果冻的地方,不可能真地把它切成几份。
按黑格尔的说法,由几部分组成的表面现象是一个错觉。唯一的真实是绝对理念,即黑格尔的上帝。我曾一度从他的哲学中得到安慰,按他的信徒们向我传授的黑格尔哲学,尤其是我当时的亲密朋友麦克塔格特,黑格尔哲学显得既迷人又可论证。
哲学家麦克塔格特长我6岁,终生都是黑格尔的虔诚信徒。他对同代人的影响颇大,我也曾一度受其影响。使自己相信时间与空间不是真的,物质是幻觉,世界实际上不是由事物而是由精神构成,这样想给人以一种奇妙的喜悦。
然而,当我猝然从门徒转向师傅,却发现黑格尔的学说是堆混乱的大杂烩,在我看来并不比双关语强多少。因此,我放弃了黑格尔哲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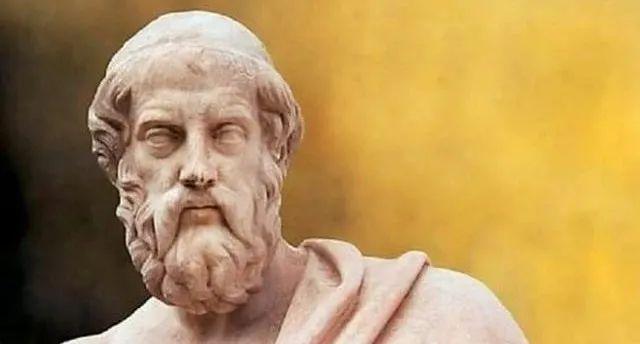
有一段时间我从一种衍自柏拉图思想并有所加工的学说得到满足。我接受的只是这种打了折扣的学说。根据柏拉图的学说,存在一个不变的永恒的思想世界,而现实世界提供给我们感官的则是它的不完善的复制品。
根据这一学说,数学可以反映思想世界,而且还具有确切性及完善性,这是现实世界无能为力的。这种数学的神秘主义由柏拉图从毕达哥拉斯衍化而来,曾吸引过我。可是最后,我感到也不得不放弃这一学说。从那之后,我从未在我可以接受的任何哲学理论中找到过宗教能给予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