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凤凰新闻》2022年8月13日
许纪霖认为,当现实生活中出现了难以承受的不确定性,在巨大的压力下,年轻人的力比多就会流向另外一边,也就是虚拟世界。因此,这个社会要想拉回年轻人,重获他们的力比多,就需要提供现实世界的“梦境感”,要让后物质主义的这一代人活得不憋屈,活得快乐。
作为一个研究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的学者,一直以来,许纪霖都对个体人物很感兴趣。这几年,他将自己的关注重心一部分转移到当下,开始研究都市年轻人的生存处境。这种转变,既与他的学术背景相关,也与他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的职业相关。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
上世纪90年代,许纪霖计划做一个有关中国知识分子代际更替问题的研究,他初步设计了框架,将中国20世纪的知识分子归为六代人,后来搁置了,没做成。但从那时起,他对知识分子代际问题尤其是年轻群体的涌现便开始格外关注。许纪霖在大学任教至今,已有40年时间,他最大的学生是“60后”,现在最年轻的学生是“00后”,他认为“作为一个好的老师,必须和学生是有沟通的,了解他们、理解他们”。因此,关注当代年轻人,特别是针对一、二线城市的青年精英群体研究成了许纪霖的新课题。
理性的保守策略
三联生活周刊:您把现在中国的主力群体分为三个大的代际,“50/60后”、“70/80后”以及“90/00后”。我们现在讨论的年轻人集中在“95后”到“00后”,在您看来,这一代人身上最大的时代特征是什么?
许纪霖:五六十年代的人经历过早期启蒙,也是在红色文化熏陶下成长的,用崔健的话来说是“红旗下的蛋”;七八十年代的人是过渡的一代,兼具上下两代人的特点,既有理想主义的一面,也有现实主义的一面;但“90/00后”则完全是新人类了,尤其是95年以后出生的“Z世代”青年,或许可以称他们为“国旗下的蛋”,他们是天然“红”,天生很爱国,因为他们出生长大的年代是中国崛起的时代,这种国家认同感是一个显著特征。这是一个大的前提。
但是这种爱国又与老一辈的爱国不同,老一辈人的自我和家国是紧密绑定的,而年轻一代对这二者的态度是分离的——他们对国家前途充满信心,但对个人未来忧心忡忡。他们不太关心宏大叙事,淡漠于国家、天下的一些大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关心社会,他们会对微观领域的事,比如动物保护、自然生态、民工教育这些具体问题感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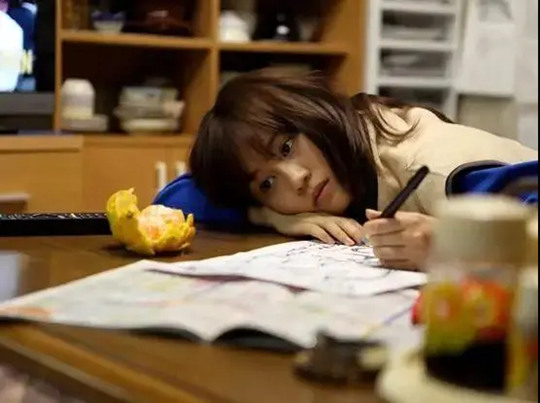
《不求上进的玉子》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近两年,年轻人考公、考编异常火热,进入体制内、“上岸”成为大多数年轻人的愿望,因此很多人认为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保守,您认同保守这个说法吗?
许纪霖:我比较认同。按理说年轻人应该是激进的,有冒险性的,会对未来抱有无限可能性的想象,这些都是年轻人的特点。20年前或10年前,年轻人就是这样的,大批“211”“985”高校的毕业生不肯进体制,他们要去创业,去追梦,敢闯、敢想、敢干,而且不怕失败。
但是这10年来,情况明显不同,年轻人越来越“不敢”。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以来,未来变得很不确定,这种不确定不仅是年轻人的感受,也是社会上下共同的感受。过去人们觉得未来是确定的,相信明天会比今天好,但今天谁都没这个把握,未来变得不可把握。所以在这个不确定的年代里,年轻人特别想要一种确定性,要追求自己的安全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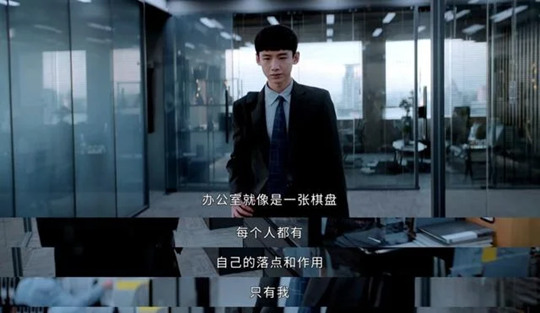
《平凡的荣耀》剧照
这种安全感首先就要安放在职业上。因为有了职业做依托,未来的个人生活才有想象的可能性。保守、稳妥、怕冒险,确实概括了今天青年一代的新趋势,但这不是贬义的。
三联生活周刊:这是他们做出的理性的选择。
许纪霖:是的,这个保守策略是蛮理性的。也就是说,在一个不确定的年代里,首先要守住阵地,以后有机会再出头,这没有问题。问题在于这成了一种集体选择。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未必意味着整体是理性的,这恰恰说明整体是不理性的,因为一个国家是需要至少有一部分人拥有冒险精神的,有冒险才有创新,才有活力。
在一个社会里,保守和激进需要一种对冲,都是激进的,这个社会可能会很莽撞,但都保守,社会就没了活力。通常来说,中年和老年是一个社会里相对保守的群体,年轻人扮演激进的角色,但现在这种平衡的、对冲的力量在减弱,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三联生活周刊:既然我们已经意识到这种“集体性保守”的趋势,该怎么做来改变现状?
许纪霖:首先要找回确定性。这个确定性不是说经济一定要向上才是确定,而是可预期。“可预期”的意思是,即使是发生了经济上的某种衰退,但依然是可预期的。经济之外,制度和政策的确定性是重要的保障。比如上海刚刚经历过长达两个多月的封控,小微企业的创业者首先遭受重创,这就是极大的不确定性,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年轻人的冒险欲望。也就是说,社会环境需要给年轻人提供一个不保守的空间。
年轻人是需要梦境感的。当遭受现实的种种不确定、不如意、挫折感,被困在这个压抑的系统中时,他们的梦境感就会转移到虚拟世界里。游戏、动漫、科幻、VR甚至是剧本杀,都是在现实世界之外制造出的“梦境”,这也是当下都市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个人在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中,往往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在现实世界里无法实现的,他们会投射到虚拟世界中去。

在美剧《人生切割术》中,个体打工者与技术推进下的现代工业社会之间的矛盾令人深思
我们一直在说年轻人保守,其实这种保守是一种“假象”。年轻人总是拥有力比多的,那种内在的激情是会投放在各个领域里的,当现实生活中出现了难以承受的不确定性,在这么大的压抑机制下,他们的力比多就会流向另外一边,也就是虚拟世界。
那么如何让他们对现实世界多上点心,在现实生活中变得不保守,就是要给年轻人制造梦境感,把他们内在的激情疏导出来。
当然,要改变社会是很难的,但作为一个公司老板、高管,或是大学校长、班主任,甚至包括家长,是否可以在小环境里让他们舒畅一点?让他们不再蜷缩起来?虽然现在的大环境不好,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是活在小环境里的,不是活在大环境里的,这是两码事。我们能做的,是改变小环境。
“年轻人的理想是此刻、当下、瞬间的快乐”
三联生活周刊:如今很多年轻人在刚毕业的时候,不得不选择“被迫性工作”或“分配性努力”,即便如此,还要面临“内卷”。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许纪霖:有关“内卷”,已经讨论得太多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内卷”,多半已经是泛化了的概念,其实是“被内卷”,并不是一个自觉的选择,而是被动的选择。现在全球都流行绩优制,我把它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2.0版”,哈佛大学的网红教授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专门写过一本《精英的傲慢》,来批判绩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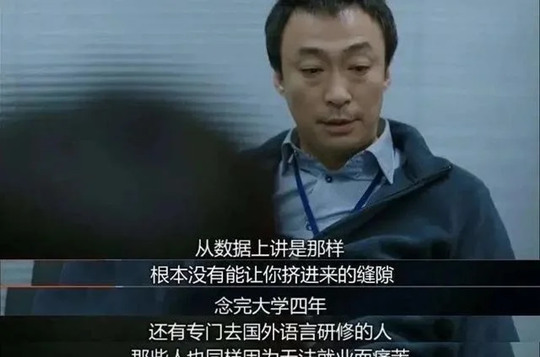
《未生》剧照
这种绩优制固化了今天的竞争,只要智商够高,再付出努力,就能够得到你想得到的,若是够不到,就说明你要么智商不够,要么努力不够。在这种绩优制的评判标准下,就会导致越来越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它看似形成了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具有合法性,大家都认可这种竞争模式,但它实质上并不平等,因为大家并不处在资源分配公平的社会环境中。就像前些天我看到一个北大的学生说,现在身边已经基本看不到一个真正从农村出来的同学了。当这些机制造成社会的固态化时,社会流动减缓,分化增大,就会造成一部分人在绩优制的系统里“内卷”,一部分人会将“一切归结于命运”作为托词,因为这种绩优制让他看不到希望,便只能选择“躺平”。
三联生活周刊:他们认为自己在做着毫无意义的工作,所以“躺平”。
许纪霖:是的。他们的期待、希望都和工作没什么关系,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们去虚拟世界里寻找梦境感,或是在现实生活中做一个副业,各有各的活法。“躺平”是“90后”的一个特殊现象,除了极个别优秀的人,大多数人看不到自己的未来,所以只能用这种方式。但一部分“躺平”的人也是危险的,我称他们是“身躺,心不平”,身躺下了,但是内心是不平的。他们对现实感到不满,对不公平的现状愤愤不平,从而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因素。

《我,到点下班》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您谈到的这种绩优制,其实也造就出了最早一代的“鸡娃”,他们刚好成长为现在的年轻人群体。
许纪霖:我的理解是,不管是谁,人活着其实都想获得一种认同,这个认同一是别人对自己的承认,二是自我的认同,所以对认同的追求实际上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追求,一般人看不到,以为追求的是具体目标,实际上都是追求一种认同,而这个认同又和自我的尊严是有关系的。
从“鸡娃”开始的“内卷”,很明显,上一代人希望把自己未能获得的自我认同转移到下一代人身上,明知前方是独木桥,但还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把别人的孩子挤下河去,让自己的孩子过那座独木桥。这其实是一个社会保守的现象,说明今天人们的选择越来越少了,只认同一种活法。

《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刚刚我们也聊到了经历过80、90年代的人是充满理想主义的,而理想主义在这个时代正在慢慢淡去。您觉得理想主义是一个有时代感的词吗?当下的年轻人还适合谈理想主义吗?
许纪霖:现在的年轻人不太愿意用这个词,他们觉得太空泛。因为说到理想主义,好像总是有一个被给定的东西叫理想。我个人的观察是:年轻人觉得不要跟我谈这个东西,“理想”已经够奢侈了,还要“主义”?他们反而觉得,要超越“理想主义”这个东西,要解构它,不认同,不反抗,也不care,他们对很多事情都是持一种虚无的态度,就按照自己的本性来活,随心所欲地活。但现实又不那么随心所欲,很多年轻人对包括家长、老师和上司等各种权威的应对方式是:态度诚恳,坚决不改。
这种随心所欲又不是真正的随心所欲,不可能不受到时代潮流的影响。在时代的潮流下,新一代的人希望做一个潮人,被潮流认可,更自我,但可惜的是,他们的自我选择能力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强,这个自我也不是真正的自我,因为真正的自我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是不跟着潮流走的,知道自己真正要什么。除了少数精英之外,大部分年轻人是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他们只是跟着潮流走而已。

《我,到点下班》剧照
这代年轻人不是没有理想,他们的理想是不被给定的,更微观、更个人化。在我看来,他们生活在表层,而理想主义者总是追求某种深刻。因为它总是伴随着某种深层的信仰,或者和宏大叙事、永恒命题相关。年轻一代人的理想是此刻的、当下的,既与历史传统切断关系,也不屑展望未来,他们要的,只是当下的、即刻的快乐。
你可以说这是一代“保守的年轻人”,但在做出价值评判之前,需要的是准确地理解他们。而理解,正是交往和沟通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