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20200617
对于全球化来说,2020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人类经历了一场真正全球化的灾难——新冠疫情。
在19世纪,霍乱要经历三年时间才能走出孟加拉,传遍印度次大陆,进而扩散到中国。而如今,任何一个世界性大都市每天都将数以十万计的旅人送往世界各地。病毒传播所需的时日甚至短于它的潜伏期。从马匹到帆船,到铁路,到汽车,再到飞机,人类不断加快自己旅行的脚步,但与此同时,病毒也加快了扩散的步伐。
如今,贸易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频繁的旅行随之而来,正如很多人所言,新冠疫情这类事件的出现只是时间问题。
因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致使英国思想史学者彼得·沃森(Peter Watson)滞留美国,他对英国、美国、中国和瑞典的防疫措施也各有评价。正是在此期间,彼得·沃森接受了新京报的采访。在他看来,我们必须在更广阔的历史尺度来理解疫情:正如历史上那些大瘟疫一样,新冠疫情传达的诸多讯号,未必能被我们立即察觉。
彼得·沃森(Peter Watson,1943— ),英国思想史学者,曾任剑桥大学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新社会》杂志副主编,为《泰晤士报》、《纽约时报》、《观察家》等报纸撰写过专栏,以拒绝简化的恢宏思想史作品闻名于西方世界,著有《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20世纪思想史: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德国天才》、《大分离:新旧大陆分道扬镳的历史》等。
在彼得·沃森看来,迄今为止,要说清楚新冠病毒为何会有如此强大的破坏力也许为时过早。研究进化论的科学家已经意识到,微生物正在采取越来越“聪明”的进化方式。而新冠病毒之源,至今也仍是未解之谜。在历史上,人们会把疾病归因为几类超自然因素。如今,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历史上彗星或陨石曾撞击地球,曾引起地震、海啸,或使大气层充满尘埃。这些环境的急剧变化催生出大范围的传染病,数以千万的人类死亡,他们腐烂的尸体变成无人知晓的微生物的温床。
通过科学考察,我们发现爱尔兰、德国和美洲的树轮形态、殷商的记载、以及北极的冰芯记录都能彼此联系起来,而在这些表面联系之下,更为深层的要点在于,地球历史上曾经突然发生过许多灾难性事件,而人类只能对此进行适应。
我们是否真的理解那些自人类进化之初便与我们共同生存的病菌与病毒?我们是否真的理解全球化时代的灾难,以及人类共同背负的命运?彼得·沃森警示我们,达尔文进化论会将人类带入一种错误的安全感中,这样的错觉不应继续下去。
采写丨陶泽慧
(《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20世纪思想史: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责任编辑)
1、十九世纪后半叶,医学世界的改变翻天覆地
新京报:病菌、病毒自始便与人类同在。当人类放弃了相对分散的狩猎采集生活方式,选择发展农工业并最终定居城市,传染病流行的风险是否必然随之增加?
彼得·沃森(以下简称沃森):伴随早期人类渐渐放弃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最终选择在城市生活时,人类社会发生了两件事情。首先,我们远离了野生动物,与驯化的动物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不同于驯化动物,野生动物族群会对疾病产生抵抗力,因为根据进化论的观点,当生物在自然环境下生存时,只有最健康的个体才能活下来。
对于传染性疾病来说,个体与个体之间的邻近关系非常重要。自然界许多物种有着“领地本能”,也就是说,如果某一个体侵犯了另一个体的领地,它们就会一较高下。借用当下流行的话语来说,这种由觅食等需求催生的“领地本能”实际上是为了 “保持社交距离”,这种残酷方式对种群健康产生了影响。许多动物都很自然地在彼此之间“保持社交距离”。
然而被人类费力养活的驯化动物(牛、羊、山羊、马)则不然,它们往往能够适应群体的生活,而人类又常常与驯化动物为伴,在这个过程中,许多疾病就开始从驯化动物传播给人类。
历史的部分魅力就在于,许多历史事件虽然同时发生,最初并无相互关联,但随着时间进展,它们开始产生复杂的关联。人类之间的邻近关系就是最典型的范例。随着人口越来越多,人类的武器越来越有威力,人们被迫生活在筑有围墙的城镇和城市里,与他人的距离也越来越近。与此同时,基于新能源的发现,交通工具也不断地进步,马匹、马拉车、帆船、蒸汽船、铁路、汽车、飞机等应运而生,更多的人都能更高效地移动起来。原本,传染病患者的寿命相对有限,但随着旅行速度的加快,疾病传播的可能性成倍地增加。在中世纪,藏在船上的老鼠带来了大瘟疫,尽管当时的人并不知道。
如今,贸易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频繁的旅行随之而来,正如很多人所言,新冠疫情这类事件的出现只是时间问题。但是,正如很多行业一样,绝大多数人及政府往往在大灾难或丑闻真正发生时才幡然醒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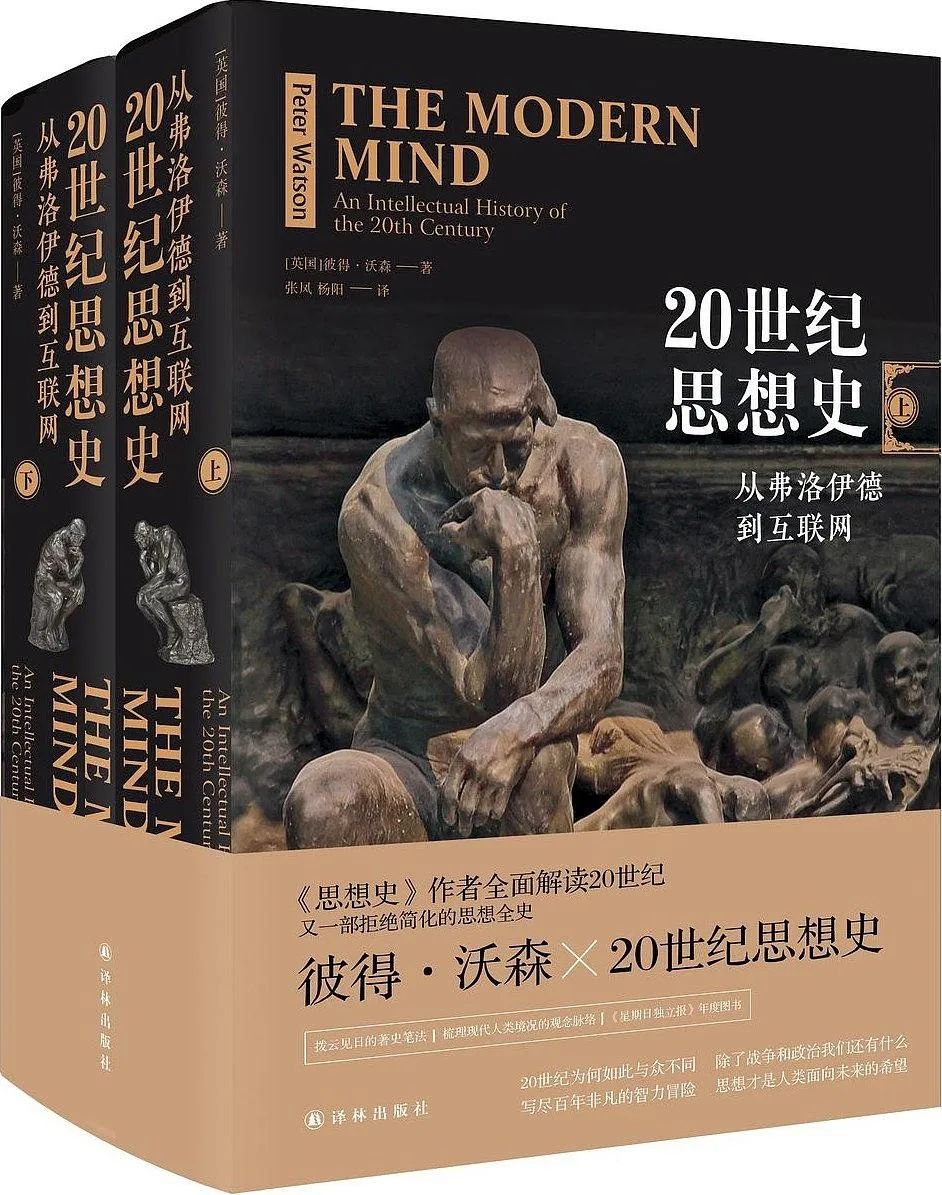
《20世纪思想史: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 [英]彼得·沃森 著,张凤 译,译林出版社2019年10月。
新京报:病菌和病毒的存在,先于我们对它们的认识。在我们开始理解致病机制之前,人们是如何理解传染病的?
沃森:直至十七世纪,显微镜的发明才使人们得以观察微生物的世界。人们第一次意识到,即使在再普通不过的水中,也存在着非常微小乃至肉眼无法看到的蠕动的生命体。在此之前,病菌的概念并不真正存在。即便显微镜发明之后,也要经历漫长的时间,人们才开始将病菌看作是致病的病原体。
此前,人们会把疾病归因为几类超自然因素,比如,古典世界里的疾病之神、魔鬼的把戏,或是女巫的诅咒。后来,疾病被设想为是人们没有履行上帝的计划,未能过着“清白的”道德生活所致。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人们认为无神论者比信徒更容易得病。
如今,我们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过去的历史中,彗星或陨石曾撞击地球,引起地震、海啸,或使大气层充满尘埃,引发我们一直都惧怕的“核冬天”。这些环境的急剧变化也催生出大范围的传染病,数以千万的人类死亡,他们腐烂的尸体变成无人知晓的微生物的温床。在过去,人们认为这是没有按照正确方式崇拜神明而招致的惩罚。玛雅人一次会献祭数千名人牲,以预防灾难的发生。也有一些证据表明,犹太教是在这类诉求下诞生的。
新京报:在历史上,人类为了对抗病菌和病毒,发明过哪些有效的方法?在你看来,哪些是重大突破的时刻?
沃森:在人类与病菌疾病所做的斗争中,真正重大的突破发生在十九世纪。在这一进程中,有几个名字尤其值得一提:英格兰人约翰·斯诺、匈牙利人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德国人罗伯特·科赫,以及法国人路易·巴斯德。
1854年,斯诺调查伦敦的一次霍乱疫情时,发现是不洁净的水源导致了疫情的暴发。他及时封锁水源,从而阻止了霍乱的扩散。不过,还要再等上二十八年,人们才真正发现致病细菌。
塞麦尔维斯通过观察发现,只要让外科医生在给不同的产妇接生的间隙洗手,就可以减少产褥热的发病率。
科赫分离出了霍乱、炭疽病和结核病的病原体,他还为细菌学奠定了科学根基,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人类现代生活的安全。他取得的进步离不开光学的最新发展,这使他能够辨析更加微小的生物体。科赫和路易·巴斯德的贡献,使得19世纪80年代的世界逐渐摆脱源自印度地区的霍乱。科赫的思想成果,最终帮助世界找到了对付猪丹毒、鼻疽病、伤寒、白喉、猪瘟、疟疾和黑水热的方法。对于个体来说,这应该算是不赖的成就吧。正是基于他的研究,人类社会通过了第一部有关传染病的法律。1907年,德国科学家保罗·埃尔利希发现了治疗梅毒的方法,并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人类免疫系统的反应机制,从而催生了抗生素的科学和医学研究。可以说,十九世纪后半叶,医学世界迎来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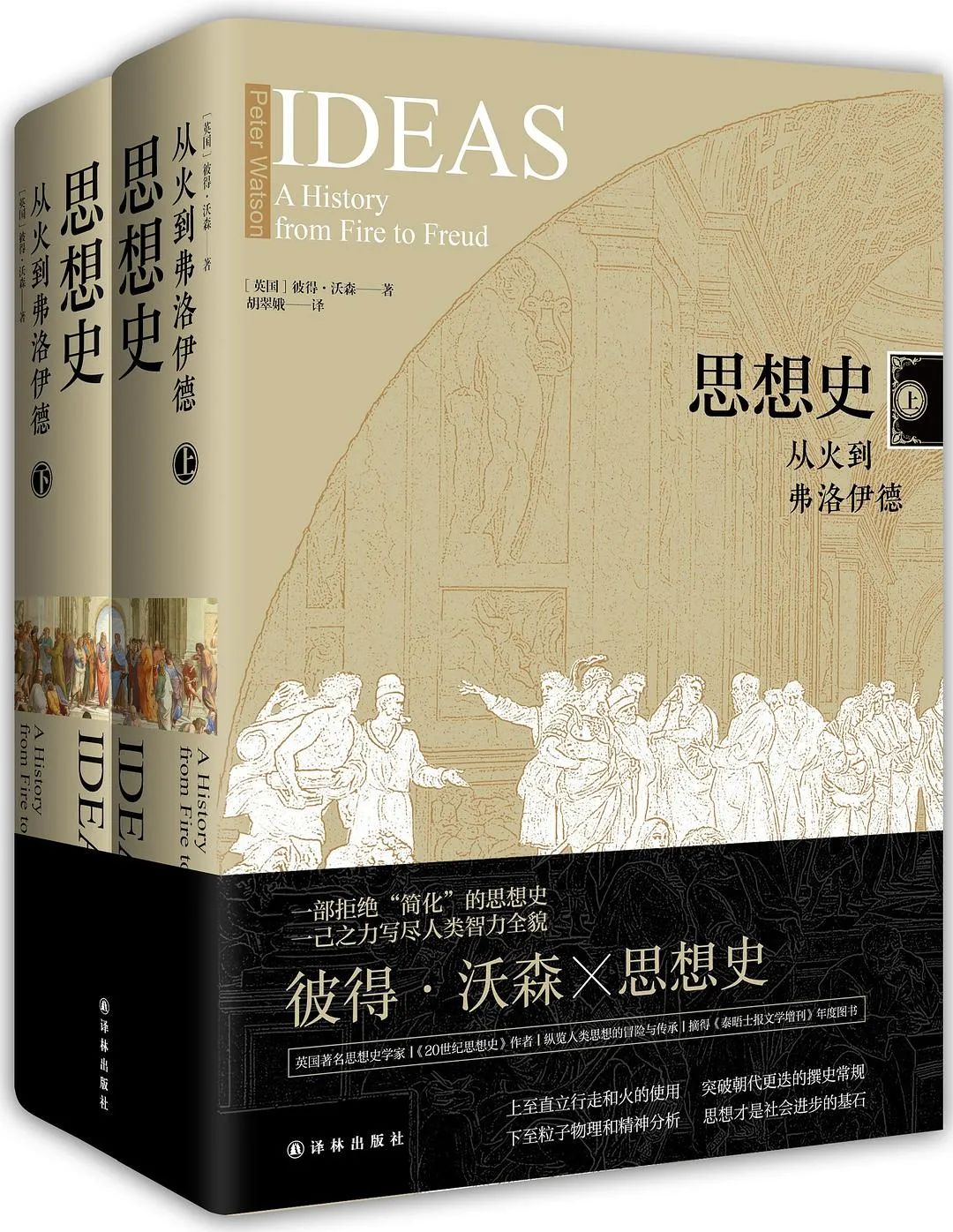
《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 [英]彼得·沃森 著,胡翠娥 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1月。
2、“群体免疫”不是有效出路
新京报:新冠病毒已成为1918年大流感以来破坏力最强、影响最深远的传染病了。新冠病毒有什么特点,能够彻底扰乱我们的现代医疗系统?从1918年至今,我们取得了多大进步?
沃森:这是个好问题。许多历史学家都曾问过,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到底是一个创新的时代,还是一个思想整合的时代?毕竟,我们这个时代绝大多数伟大发现和“技术应用”都诞生于1850年到1950年间前后,不论是电灯、打字机、电子和无线电,还是电视、汽车、铁路、飞机和抗生素……从那以后,除了互联网技术的精妙组合应用以外,人类的成就更多基于对于此前技术的提炼。
从二十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一世纪,医学和生物学的重大进步主要产生在精神病学、心脏和中风治疗、癌症治疗等领域。这主要是因为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大部分病菌疾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可是在最近几十年,艾滋病、非典和中东呼吸综合征等疾病的出现又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应该警惕此类问题对整个人类的风险。
迄今为止,要说清楚新冠病毒为何会有如此强大的破坏力也许为时过早。研究进化论的科学家已经意识到,微生物正在采取越来越“聪明”的进化方式,它对我们人类来说也变得越来越难以理解。一些早期证据表明,新冠病毒实际上存在不同的菌株,它们彼此之间存在微妙的差异,却在医疗上表现出相当不同的症状,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只有轻微的症状,而有些人的症状却很致命。这也许便是有些感染病康复的人并没有获得完全的免疫力,可以再次感染的原因。时间会将现实展现在我们面前,但就传染病学而言,我们确实面临着一种前所未有的状况。

彼得·沃森
新京报:你如何评价英国、美国和中国的防疫措施?三个国家对于疫情的理解是否有所不同?
沃森:传染病对某些西方国家来说可能是个严重的问题。美国的情况已经告诉我们,这一类国家并不善于采取集体措施。人口的数量和分布显然和疫情有很高的相关性。美国是个大国,既有人口密集的城市,也有许多人烟稀少的中西部州。不同地区的感染率会截然不同。英国或者说西欧则和中国比较相似,有些地区人口非常稠密。在我多次造访中国之后,我留下的印象是,那里的人民更情愿接受政府的集体措施和管理。换句话说,他们愿意听从政府的告诫,因此隔离和封锁的命令都执行得比较迅速和彻底。
在英国,民众难以接受这一点,并在较长的时间内继续维持着较为喧闹的公共生活。实际上,这并非明智之举。美国和英国的政府无疑反应迟钝,一开始还以为“群体免疫”可能是有效出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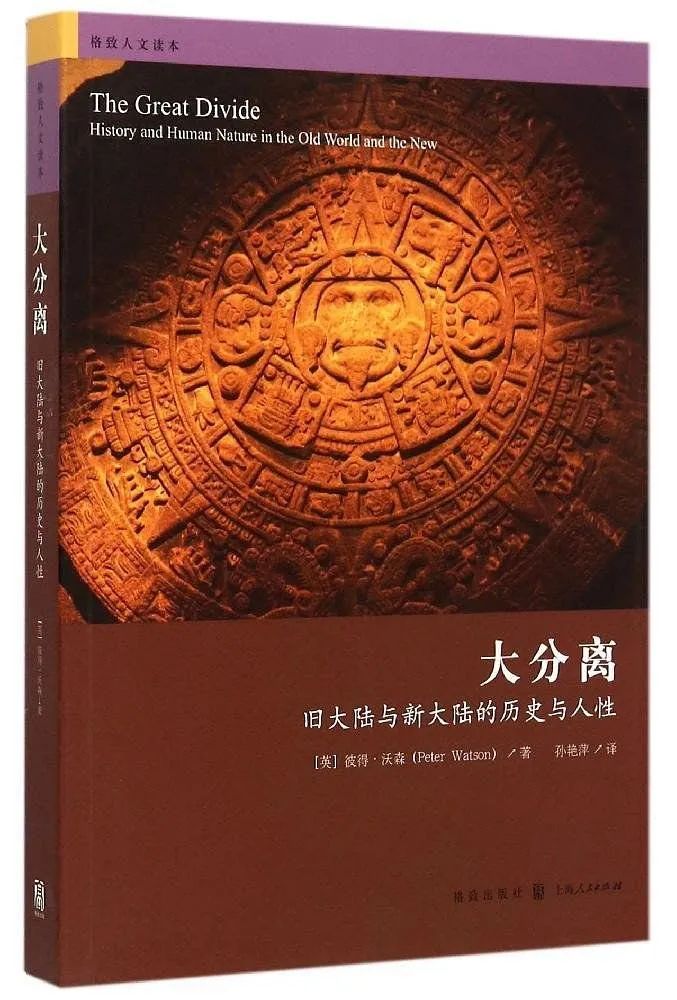
《大分离:旧大陆与新大陆的历史与人性》,[英] 彼得·沃森 著,孙艳萍 译,格致出版社2015年8月版。
3、新冠疫情传达的信息,我们未必能够立即察觉
新京报:你在《大分离》中强调了新旧世界的差异,当旧世界的人发现了新大陆时,他们携带的病菌和病毒给美洲土著带来了超乎想象的灾难。你在《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和《20世纪思想史: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两本书中也写过,传染病改变了人类的面貌,催生出思想的进步。在你看来,当下的疫情会给人类带来怎样的改变?我们能否从中受益?我们需要为此类灾难做哪些准备?
沃森:就目前而言,这个问题可能不是最重要的,但在我看来,它有长远且深刻的意义。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很大。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发现新大陆,最先来到美洲的欧洲人不仅带来了战争与征服,还携带着包括天花在内的各种传染病。玛雅人和印加人对这些疾病毫无抵抗力,因此遭受了灭顶之灾。传染病塑造了今天的美国,而美国人往往忽略了这一点。
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例,那就是“黑死病”。人们曾为黑死病的历史后果挥洒过很多笔墨。比如,在十四世纪,由于黑死病的影响,欧洲很多乡村地区都缺少人丁。这迫使许多地主不得不屈服于农民的需求,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我们在许多考古发现中也证实了这一点,例如,在这一时期,很多原本使用陶器的场合开始使用金属器皿。黑死病也给教会和宗教生活带来了两大影响。首先,大量的死亡使得人们变得悲观,也促使他们转向内心,实践更为私人化的信仰。大瘟疫之后,许多私人教堂和慈善机构随之设立,神秘主义也开始兴起。此外,人们对基督圣体也愈发关注:瘟疫前不久,梵蒂冈大公会议曾规定,天主教徒应每年至少领受一次圣餐,瘟疫过后,天主教徒则力求尽可能频繁地领受圣餐。
与此同时,许多人也走向相反的心路历程,开始怀疑是否真有一个天主能够掌控世界的天命。大瘟疫的第二个重大影响落在教会的结构上:大约40%的神父患病去世,在许多情形下,教会不得不动用非常年轻的神职人员,取代那些病逝的神父。这些年轻神职人员的受教育程度远不如他们的前辈,这使得教会在神学领域的权威性大打折扣。天主教的宣教在许多方面都迎来了崩溃。
我之所以谈及这些,是为了说明传染病带来的许多重大影响并不能被立即察觉到,它们常常及其复杂,同时存在于许多层面,并将延续很长的时间。在我看来,新冠疫情将会有一个相对长远的影响。
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我们已经对历史(哪怕是深层历史)产生了某种定式思维,我们认为历史由一长串微小的进步组成,世界在这个过程中缓慢地改变。我们可以将这样的世界称作一个后查尔斯·达尔文、后查尔斯·莱尔、后格雷戈尔·孟德尔、后粒子物理学的世界,这是一个缓慢进化的世界,它的步调缓慢到几乎处于持续的稳定之中。
但现在,人们对历史的实质产生了不同的理解。这种理解的出现吸纳了植物学家、地质学家、天文学家、历史学家(尤其是神话学者)的研究工作。他们的成果表明,许多自古流传下来的神话(无论是出自爱尔兰西部、古希腊,或者中国)呈现出一种思想上的连贯性。这些经过破译之后的神话告诉我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地球曾遭受一系列灾难性的突发事件的侵袭。这样的灾难事件可能由彗星和小行星导致,可能是地震、海啸、日食,以及能屏蔽太阳和月亮达数月之久的沙暴。史料显示,这些灾难事件往往伴随着瘟疫,每次灾难可能都会有数千数万人死去,幸存者没有能力埋葬他们,只能任由尸体腐烂,任由感染肆虐。
通过科学考察,我们发现爱尔兰、德国和美洲的树轮形态、殷商的记载、以及北极的冰芯记录都能彼此联系起来,而在这些表面联系之下,更为深层的要点在于,地球历史上曾经突然发生过许多类似通古斯大爆炸的灾难性事件,而人类只能对此进行适应。
通古斯大爆炸发生在偏远地区,而我们地球的十分之七由海洋组成。因此,历史上冲击地球的外来天体也并非总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破坏。但有越来越多证据表明,突如其来的灾难确实促使我们的祖先进行反思。例如,英格兰南部著名的史前遗址巨石阵,最近就被重新解释为一种天文计算器,古人试图通过它来预测下一次灾难的发生时间。
在我看来,这才是新冠疫情应当传达的讯息。当历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予以我们迎面痛击的时候,达尔文进化论会将我们带入一种错误的安全感中。这样的错觉不应继续下去。
疫情过后,“全球化”是否会走向终结?